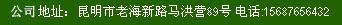|
北京中科医院亲身经历 https://m.39.net/baidianfeng/a_5154121.html 原文作者:吴长青,文学博士、安徽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干(来源:互联网)伴随着新世纪进入第20个年头,新写实文学思潮也随着新时期以来主流文学思潮的跌宕起伏,从夹缝中生长到蠢蠢渐入中心的态势,漠视它的存在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批评家王干作为新时期以来文学主潮的推手一直活跃在文坛上,本文借《王干文集》出版契机,通过王干文学批评的视角对网络文学作者的分化、现实境遇以及建构为一种尚在生长的文学思潮进行考察。 从20世纪80年代“新写实”思潮出发 通常意义上,文学思潮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地域内形成的﹐与社会的经济变革和人们的精神需求相适应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潮流。“先锋文学”“新写实”作为新时期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之后的两大主流,为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以来的文学格局奠定了基础,不仅培育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家,一些创作力旺盛的作家依然活跃在当下文坛。这两股思潮还对早期网络作家的成长与创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也为网络文学的生长提供了可参照的评论资源。 王干作为文学期刊编辑的职业身份和专业评论家的在场评论堪为当代文学的“活化石”,他的文学历程为我们留下了足够多的现场文本,在王干的早期的文学评论中,我们能够寻觅到21世纪前后各20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 循着《王干文集》的脉络,在“废墟之花”专辑中,王干对文学的介入是从“朦胧诗”的批评开始的。这是“先锋文学”登场的前奏,也是由于思想解放结出的精神硕果,当代中国文学重新走上了探寻艺术形式多样化之路。作为网络文学的“寻根”之旅,依然绕不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先锋文学”,作为影响当代文学的重要文学思潮,历来被后续评论家津津乐道,这其中有无限言说的空间,无论对“文学史”的意义,还是对社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透过这些活生生的现场,可以探寻到“人”在这些细节中以及这些“人”在生活细节中的状态。“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诚然,文学的核心自始至终围绕着“人”的一切,这也是我们今天追寻所谓文学意义和价值的动机和情感所在。 在王干的文学批评中我们可以读出他对那段历史的严谨审慎的思考,而不是作为叙述主体对客体的简单结论,“历时”与“共时”相互映衬的观照维度,将横贯整个近四十年的文学历程,客观冷静地与具体历史事件放置在特定的“时间隧道”里整体作考察,这样的客观性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王干对历史的一种敏锐的“先锋”批评意识。这为我们今天判断文学史的圈层结构,乃至对当代文学的整体认知提供了场域和知识的双重储备。 在对先锋作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苏童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河岸》的评论中,他说:“先锋派的主人公往往是玩世不恭的,至少那个叙述者是玩世不恭的。他们是价值的毁灭者,意义的爆破者。我们今天审视这些毁灭和爆破,一点也不会大惊小怪,因为网络的爆破和毁灭让我们已经熟视无睹,而在20年前这些冒犯是要承担很多的罪责的。”这是将“先锋文学”与互联网技术对人的精神僭越语境中进行的两厢对照,当然也是对“先锋文学”作家当年的先锋性的一种肯定。这种“历时性”的判断,既有回顾与反思,更有对当下主流文学的出路与网络文学大行其道两者之间有可能形成的张力的一种预判。 王干对“先锋文学”的判断除了在具体文本中以一种安静而客观的历史目光审视之外,还将之作为“主体”放置在更大的宏阔视野上,于是,我们在历史的图谱中渐渐看清了“先锋文学”的纹理,也只有这么客观细微地观照,“先锋文学”的镜像才更为完整而详细。既回避了抽象谈文学现象,又将“先锋文学”的局部与整体进行比照,这样带给后人的将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表述,同时带着一种反思式的商榷。这其中包含着对“先锋文学”内在流变的整体性的把握。 在接受初清华采访时,他坦陈:“先锋或前卫是开枪了,但是击中的却是自己的作品,因为传统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具体实在,他们似乎在虚构传统,而传统也在虚构先锋。二十世纪先锋和传统的对立和对抗,都是一种想象,当然利用这种想象造成的裂隙是另一个有趣的研究话题。先锋文学本质是一种文化情绪,这种情绪是对一个新的生活观念,生活价值观乃至世界观的渴望,这个是后来先锋文学和传统文学最大的分歧所在。”在两厢对照里既看到了80年代“先锋文学”对传统叛逆的影子,又为我们今天谈论网络文学作了必要的铺垫,同时也为探讨网络文学能否具备“先锋性”预设了必要的论题。 谈论80年代文学,绝不是停留在80年代,而是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超级棒贵港乡村振兴答卷亮眼了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