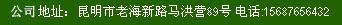|
年1月,《十月》的“头条诗人”是陈先发。《十月》以“了忽焉”为题,发表陈先发的8首诗。其实,前面已经写过一篇文章了,但只是在“中国诗歌网”上看到这组诗,只是凭自己的感觉说些话。没想到《十月》还有很多解读,甚至请了不少“著名”人士。 首先,《十月》同步推出了文河的《盲人扑蝶——陈先发长诗《了忽焉》阅读札记》,也就是读后感。同为安徽人的文河,对安徽诗人陈先发的《了忽焉》,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然后,《十月》在年1月27日,举办了“历史的耳语——从陈先发长诗新作《了忽焉》说起”的分享会会。李敬泽、欧阳江河、李舫、敬文东、杨庆祥等“著名”人士出席。中国新闻网、中国诗歌网、澎湃新闻、大皖新闻等媒体平台进行了转载报道。 图片来源于《十月》显然,《十月》这是将陈先发的《了忽焉》隆重推出来的。这些“著名”人士,对陈先发的《了忽焉》,当然也是毫无例外地一致好评。李敬泽说,“《了乎焉》是对千年前声音的回应式写作,是两种不同声音的碰撞”。 欧阳江河说,“陈先发对《了乎焉》的写作决定,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决定,是对一生写作的交代,也是历史与现实塑造下的综合行为。”作为学术主持的杨庆祥,进行了最后的总结,“精神上的呼应和对话成就了《了乎焉》,语言、历史和生命在其中发生互动、互文和互相创造,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诗歌发生学。” 与以前一样,这些“著名”人士所说的话,给人的感觉是,什么都说了,但又什么都没说。这估计是“著名”人士说话,或者是写作的通病。也就是说,这么多“著名”人士的解读,还是让人不知道陈先发的《了忽焉》到底好在哪里。 确实,这对于普通的诗人,或者是普通的诗歌爱好者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原本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去学习“著名”人士的诗歌和评论,但学习的结果是,更加糊涂了。诗歌评论,或者是赏析,就不能说具体一点吗?这首诗好,好在哪里? 陈先发的《了忽焉》是组诗,我们还是来看其中的一首《了忽焉》吧。前面虽然写过文章,但有些弯弯绕的嫌疑,这次就反“著名”之道而行之,来得直接一点。 图片来源于《十月》陈先发的这首《了忽焉》,描述了汉献帝的“弱小”和“危机”,从“棉套中人”(正常人)到“木套中人”(被幽禁)再到“铁套中人”(阶下囚),汉献帝只能装聋作哑。汉献帝的失败,是“败于乌合之众”,败于“四万万匹隐蔽的纸马”。 对于历史,陈先发总结为“无形人穿无形衣”,在这种无形的历史里,晦涩的汉献帝和老窑工融为了一体。大家注意,陈先发这首《了忽焉》,是刻在曹操宗族墓里的一块砖上的,而不是刻在汉献帝墓里的一块砖上。也就是说,老窑工在修曹操宗族墓时,为汉献帝刻下了“了忽焉”。 历史是无形的吗?历史是败给了乌合之众吗?历史是“四万万匹隐形纸马”所创造的吗?汉献帝成为“铁套中人”,是令人惋惜的吗?大家看看这几个问题,也许就明白了陈先发这首《了忽焉》的主题了。 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并不是无形的,历史不是败给了乌合之众,历史更不是“隐蔽的纸马”创造的。劳动者创造了历史,劳动者改变了历史,而不是某个什么“帝”。某个“帝”的危机,是他自己造成的,而“老窑工”更不会站在他的立场上,去“了忽焉”。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anhuishengzx.com/ahxw/15029.html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辉隆股份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