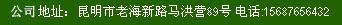|
贵州白癜风治疗中心 http://baidianfeng.39.net/a_zczz/160205/4769910.html 上善若水。老子还说,水是利万物而不争的自然物象。 逝水流年 在“我”的视域中,水,太善于成为一切了,就是不在乎成为自己!她更是一位可亲可爱的恋人,纯善而美好。一个被肺炎弄成脑瘫儿的“我”,一有时间就观察水,从小对水充满了爱的感伤。 作为伐木工,“我”四十大几却没接触过女性,寡言少语的伐木工,于真心地倾诉和赞赏中,痴恋上了一个曼舞不休的水姑娘。“我”干起活来如何不比别人差,却不愿多费口舌,听觉也不对头,总能感受到树像女人一样痛苦和哭泣。树一哭,“我“就亲一下树的伤口,大家也模仿”我“亲一下。老板的小三来了,有只百灵鸟鸣啭着,枯燥就一扫而光,大家的表现都不太像自己,老板没了骄气,伐木工没了匪气,我也不再生闷气。小美人一走,就大侃那些野合之事。 中秋节,留守的”我“拎手电,扛铁锹,穿过林子,邂逅了一挂舞蹈的水瀑布——“我”的水姑娘。她从容不迫地跳着舞,内心清清亮亮,赞美真真诚诚。探访水姑娘是”我“做伐木工初衷不改的乐趣。一遭事业有成,心有感伤的”我“,再次探访,水姑娘却芳踪杳无迹。工厂林立,溪水断流,湖水血红一片。 那种魂断原生自然的疼,无以复加。文笔流畅,妙语连珠,散思飞扬,情节简素,拟化的对白,水姑娘之像喻,邂逅原生态的欣喜与触目所见的硬殇,道不尽的爱与清愁,一篇颇有象征意味的佳作,鞭辟入理,催人反思。 水姑娘 黄梵 《作家》年第10期 逝水流年文学社团精品典藏 我小时住在热闹的小镇码头,十米外就是赫赫有名的长江,我一直喜欢我的邻居——水。乍看它脏兮兮,满身都是窟窿,但这些窟窿有趣极了,它们凹进水里只一会,就争先恐后要逃出来,没一个窟窿肯留下,去做呆在水里的空房间。难怪水里有太多垃圾没地方住,全都挤在水面,与“黄金航道”上的船只争抢航道。我一有时间就观察水,不知为什么,它们总让我大为伤感。你瞧,它们进了厨房就成为汤水和熟米,进了酒厂就成为酒,进了人体就成为血,进了眼睛就成为泪,进了瓜果就成为汁,进了教堂就成为受洗之水,进了锅炉就成为冬天的暖气。它太善于成为一切了,就是不在乎成为自己!它脏兮兮、满不在乎的样子,总是让我伤感。有一次,它进了我母亲的肚子成为羊水,就在我钻出娘肚的当口,它做了不该做的事,它竟想跑进我的肺里,想成为我的肺叶,结果害我患上了吸入性的肺炎…… 到了我懂事的那一天,母亲唉声叹气地告诉我,我是个不折不扣的脑瘫儿。脑——瘫——儿——如果我试着说这三个字,你会觉得我在说:“鸟——蛋——饿——”,速度比破折号显示的还要慢。打那以后,我就不怎么高兴得起来,一见门外的江水就伤感。我不恨它,甚至喜欢它的顽皮,但它也让我纠结得酸不溜秋。它要是没有成为其它东西的野心,该多好,那样我就不会被肺炎弄成脑瘫儿。可是,它要是不想成为别的东西,我身上也就不会流动着血,我也就没法活着成为脑瘫儿。我用眼睛死死盯着门外的江水,觉得这个问题有趣极了,里面暗含的道理,我怎么也想不透。 长话短说吧,我就不介绍自己如何成了伐木工,干起活来如何不比别人差。我惟一怕的是多费口舌。让我说话,等于是让字音从锅一样的口腔,掀开锅盖一样的舌头,跃入空气。舌头完全像个肉乎乎贪睡的海狮,根本懒得挪动沉甸甸的身子。好在伐木工无须多费口舌,说话是老板木材商的份内事,他叽叽喳喳起来,舌头就像输送字音的传送带,与我在矿山见过的传送带一模一样,脏兮兮的,发黑,粘满油脂,散着我不喜欢的沼气味。幸亏我说话少,我口腔里的那头“海狮”,向来倒干干净净的。 近来,我又觉得听觉不对头。以前伐木的时候,除了小鸟,只会觉得几个伐木工是活物。他们用电锯伐倒几棵树,就会歇下来,泄愤似的骂一会脏话,接着津津乐道男女之事。我喜欢在巨大的电锯声中,辨听那些渺不足道的鸟鸣声。现在,林子中有别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且越来越多。自从我听到第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喊,尖叫、哭泣、咒骂,就渐渐充塞了我的耳朵。这些令我越来越内疚的声音,全部来自山上的树。 “你们听!它们在哭!”当我用夸张的口形,艰难地提醒伐木工们,竟没有谁当回事。“闷头(我的小名),是你脑子里的小娘子在哭吧?!你可得好好哄哄她哦!”说罢,他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闷头,别理他们!我和你一样心疼小娘子,快说说她到底怎么啦?” 我不喜欢其他人的假仁假义,于是把他拉到一边,让他把耳朵贴着树,想把树的痛苦传递给他。我把兜里收拢的水果刀掰开,用刀子削下一块树皮,顿时,树的痛苦叫声令我差点淌下眼泪。 “你听见了吗?”说来也怪,我以前听到的叫声一直没有性别,可是现在,它分明是一个女人的尖利嗓音。 “听到了,听到了!好甜的嗓音哪,难怪闷头被迷住了!”他把脸扭向他们,说罢又抱住树,在树的伤口上使劲亲了一下,“哈哈,我尝到小娘子的哈喇子了,甜甜的,香香的!”其他伐木工们一时愣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连脸上的皱纹都像礁石一样凝固着,接着他们回过神来,蓦地大笑起来。笑完,他们二话不说,一个接一个走向这棵树,学着他刚才的样子,每人对着树的伤口猛亲一下。 “闷头,你这下满意了吧?你看,我们多喜欢你的小娘子!” “是啊,小娘子漂亮极了!来来,快把你的电锯拿过来,这回你得亲自把小娘子放倒,再抱到你床上……” 他们笑得眼里都噙着泪珠子。一旦我察觉到,他们乐不可支的笑声,含着淫邪的嘲弄,我又回到了孤身一人的世界,不高兴再跟他们说什么真相。哪怕第二天他们又百般挑逗我,看着我的盒饭说,你碗里的干豇豆身材真苗条,可惜年龄太大了,你倒吃得这么欢,真是来者不拒啊。我愣是不吭声,甚至给耳朵塞上了棉花,这样心里除了闷得慌,耳根子倒清净起来。林中那些一直抽打着我的哭声、叫喊声、咒骂声,也被耳里的棉花,滤得寥寥落落…… 中秋节的前一天,老板突然爽快起来,宣布除了法定假日,再多给大家放三天假。伐木工们纷纷挤眉弄眼,我知道他们想说什么。是啊,要不是老板的漂亮小三吹了什么枕边风,老板哪会对我们这么仁慈呢?老板常带小三来林场,她看上去像个小他很多岁的少女,她喜欢看伐木工如何把树伐倒。我发现,老板和她说话时,她倒有些心不在焉,仿佛一时半会找不到舌头。她最喜欢围着伐木工们打转转。她一来,伐木工们就不说脏话了,个个把自己憋得挺体面,莫非是她脸上的稚气,让他们想到了做父亲的责任?她一到林子里,就像百灵鸟找回了有甜润声音的舌头,说笑声宛如百灵鸟的鸣转,在我胸中激起能忘掉劳累的欢乐。 每当此时,就见老板在胸前交叉着双臂,乖乖当一名听众,大家也忘了世上还有他。伐木工们夸小三是唱歌的天才,嗓音清脆、嘹亮,他们不光爱听,也个个摩拳擦掌来和她赛歌。有个西北来的汉子,能把山歌飚到了不起的音高,唱完,震得大家都说不出话。每到这时,就轮到老板出场了——他会像孩子一样拼命鼓掌,吹口哨,引得大家也怂恿他来飚歌。老板在小三面前谦虚极了,总说他的嗓子上不了台面。说来也怪,只要小三一来林场,大家的表现都不太像自己,老板没了骄气,伐木工没了匪气,我也不再生闷气。可惜,小美人(伐木工们背地对她的昵称)带给大家的美妙时光,犹如昙花一现,每次等林中的“联欢会”结束,小美人当然又归老板独享,他会带着她,神神秘秘地走向林子深处…… 小美人一走,伐木工们马上判若两人,又把说脏话当成了大乐子,直说得我心惊肉跳。他们说老板带着小美人到小瀑布那边野合去了,说他俩喜欢一丝不挂,站在瀑布中央野合。真太不像话了!我是说,他们这样偷窥别人太不像话了!他们用大蒜味很重的口气,为野合的细节争论不休,仿佛不把我说晕,绝不罢休。我被他们说得耳根发烫、额头冒汗,只好再次掏出棉花,把耳朵堵个严严实实。这种野合之事,我其实连听的资格都没有。我没有恋爱过,成过家,女人在我眼里就像一轮明月,只是被黑夜收藏的一件精美文物,我只有看的份。我年过四十,从没被女人看上过,只好认命了。认命归认命,心里的隐隐期待还是滔滔不绝,就像小时坐在江边,看那些千姿百态的水窟窿,心里却无望地期待里面会冒出我喜欢的女同学…… 中秋节期间,我无处可去,想到北上回家路上要花四天,与家人团聚的意义,就变得十分牵强,倒不如把路费省下来,汇给母亲过日子。再说,节日期间因为没有砍伐,林场格外恬静、平和,树们不再哭哭啼啼,我的心情也轻松起来。林场只剩我一人时,我突然感到身上有一份责任:我应该在林场的地盘上巡逻,防范想盗木的贼。 一天早晨,吃罢早饭,我就拎着一把铁锹,出发了。冲下一条坡道时,因躲闪不及,铁锹撞到了一棵小树,我的耳边立刻响起了尖叫声。没错,那是一个少女的痛苦叫声。我赶紧站住,用手去抚弄树上被铁锹戳出的口子。我很诧异,随着我温柔的抚弄,那棵小树的痛苦叫声,渐渐变成了嘀嘀咕咕的感谢声。后来,我在林中穿行时,一直把铁锹抱在怀里,不让它碰着那些可怜的树。就在我走得腰酸背痛,精疲力竭时,眼前突然一亮,头顶上方没了遮天蔽日的繁茂树冠,只见一条溪流像温顺的小狗,一路跑过来舔我的鞋子。我顺着脚下的溪流往上看,只见这条溪流从挺高的山上下来,到了不远处的断崖才突然喧闹起来。断崖令溪流像一群戏水的孩子,纷纷往崖下的水潭“下饺子”。 我放下铁锹时才发现,肚皮隐隐作痛。原来就算隔着一层衣服,锋利的锹刃还是掀掉了一块皮肤的外皮。看着隐隐渗血的皮肤,我索性把衣服脱了搭在肩上,一屁股坐在溪边。屁股一着地,我才如梦初醒,这里不就是伐木工们津津乐道的小瀑布,老板和小美人野合的地方吗?说来也怪,当我望着瀑布愣神的当口,眼睛竟看见了惊人的一幕:一个十分苗条的裸体女子,正在瀑布里洗澡。她对我坐在溪边完全熟视无睹,她不停扭动着好看的身躯,竭力应和着飞落的水流。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女人的真身裸体!以前孤单之极,也看过一些黄片,但那种感觉实在比不上眼前女子不经意扭动的一个身姿。她只关心自己洗澡,不在乎我直勾勾地望着她。 当我大着胆子慢慢靠近,发现她的身躯与水流居然是一体。就像旗子随风赋形,她娇嫩、精巧、动人的身姿,其实由变动不居的水流造出。我一时诧异、困惑,摸不着头绪。就算我看出,她的身躯就是水流的一部分,我还是感到脸颊和耳根发烫,心里刹那蹦出了一个词:水姑娘。 “喜欢看吗?心满意足了?” 看得入迷的我,被耳边的嗓音吓了一大跳。 “你,你是在对我说话吗?”我努力把字音吐得清楚些,但还是被舌头弄得一团糟。我恨自己的舌头不听使唤,好不容易蹦出的字音,总是言东指西。 “对啊,这里还有别人吗?你的声音很好听耶!” “什么?你说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话要是伐木工们说的,我一定会生气,他们假模假式的夸赞里,永远夹着嘲讽。 “我说你的声音好听呀。怎么?你不信?” 我心里突然涌出了快乐,“信!信!因为你是第一个夸我的,所以,我不敢相信……” “什么?居然没人夸你?太不可思议了!”水姑娘一边说着话,一边身子像着了魔,跟着水流加快了舞动。她的脸高贵、漂亮,却没有一丝看不起我的神情。我的心开始发颤,她不就是我在漫长梦境中呼唤过的女神吗? “你一直这样跳舞,会不会很累?不穿衣服会不会受凉?”是啊,我心里一时塞满了无数的担心。水姑娘莞尔一笑,说:“我就是活在舞蹈中呀,活在无遮无拦的清泉里,要是哪天我没法跳舞了,你也就看不见我了。” “你一直不睡觉吗?” “睡呀,只不过你看不出来,我睡着了也还在跳舞。” 水姑娘越说我心里的困惑越多,“你怎么会说话?我可从来没听水说过话,只听过水哗啦哗啦乱响。” 她看着我的目光里,似有一丝怜悯,“这可不能怪水,只能怪你以前心不够静,你现在不就听到了吗?你不觉得你现在的心很静吗?” 我点点头。她一开口,我就觉得自己很浅薄。尽管她美丽的身躯就是水流,我一点也不沮丧,相反,她婀娜多姿的身躯,完全囚住了我的心身。 “我可不可以……搂一下你的腰?”话刚出口,我就臊得两颊发烫,诧异自己竟会冒出这么放肆的话来。 “好啊,没问题!但你要有心理准备,会吓着你的!” 我的兴致正高,当然不会被这话吓倒。我犹豫片刻,慢慢把手伸向她那摇曳不定的蜂腰。手触到她腰的一瞬,并没觉得水的冰凉有什么特别,但我眼里的景象竟像恶梦。只见我的手像水流中的手术刀,硬生生切开了她腰部的肌肤,令我看见了血红的内脏。我吓得猛地收回手,眼泪差点淌了下来。说来也怪,手一离开水流,她的腰就立刻恢复原状,仿佛没受过任何伤害。 “吓着了吧?不过别担心,你要是有兴趣,还可以把手伸到我头上,看看我的脑子,我不会受伤的。” 我拼命摆着手,“不,不了!我不碰你了,我愿意就这样永远只看着你!” 水姑娘舞动身子的同时,一直用目光凝视着我,“你真是一个好男人!少见的好男人!你知道为什么会看见我内脏吗?你过来坐下,让我慢慢告诉你。” 是啊,刚才站在她面前的激动,一直令我浑身颤栗,站立不稳。一旦坐下来仰望着她,越发觉得她美丽了,那发亮的额头和前倾的下巴,使她的脸有着无尽的魅力。 “差不多是三年前的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有了血红的内脏。在那之前,我的内脏是透明的,你就算伸手过来,也看不见它们。过去这条瀑布里有我很多姐妹,自从我们都有了血红的内脏,她们就纷纷走了。”她突然神情肃然,沉默不语。 我迫不及待地问:“她们都去哪里了?” 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有些姐妹走了,也就是过世了,有些去了下游。我和姐妹们从此阴阳相隔,或各奔东西,再也无法相见。都是山那边的工厂害的。惟一幸运的是,我对重金属的耐受力比较强,山上下来的水暂时还毒不死我……” “为什么我不碰你的时候,水还是透明的?” 我的话令她的脸上多了一丝愁容,“要是人能看见就好了,等你们能一眼看见的时候,水就能毒死你们了,但现在,水只能毒死我的姐妹们……” 我突然想到了老板和小美人,于是用有点拘谨的语气问她:“你有没有见过一男一女来过这里?男的比女的大不少。” “当然见过。那男的没心没肺,始终在虐待女孩子。不过,那女孩子也够疯的,倒也心甘情愿……”我感到脸颊又像火似的烧起来。 “那,那他们有没有看见你的内脏?”我变得不安起来。 “他们碰不到我的,他们钻进瀑布的时候,我会把身子缩得很细,躲开他们,不是谁都能碰到我的。除了你,至今还没别人能碰到我。”她的话令我松了一口气,同时心里飘飘然有了几分醉意。但我还是困惑不已,“你为什么要我看见你的内脏?” “别担心,我只是想让你永远记住我,记住我和你一样也有生命,也会死!”她把“死”字说得很重,仿佛她正被人推进屠宰场。 “为什么选择我来记住你?” 水姑娘尽力把身子弯向我,凑近我的脸说:“这还用问吗?因为你和我们一样,内心清清亮亮,你说话的声音也像我的姐妹们……” “可,可是,他们不喜欢听我说话,总说听我说话太费劲。” 水姑娘就像刚放下听诊器的医生,面对一个没病的病人,竭力安慰道:“他们?他们怎么能跟你相比?他们说的是脏话,你说的是天籁。天籁当然只有我们能听懂、欣赏,对不对?” 和水姑娘告别的时候,天色已晚。我走进林场宿舍时,心里还暖乎乎的。那一夜,我躺着怎么也睡不着,我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她。我一点也不为爱上瀑布里的这个女子后悔,她说的话,句句都撞在我的心坎上…… 第二天,我取了一盏应急照明灯,来到瀑布跟前。一直陪她陪到天色漆黑,我把灯拧亮,小心放在她脚下的岸边。她不解地问我,你又在搞什么名堂?得知我是怕她一整夜呆在漆黑里,她乐不可支地笑起来,说完全没有必要,晚上是她看星星的时间,说你好心的灯光会晃了我的眼。“看星星?”我就像撞见了喜鹊,觉得又要遇到大好事了,连忙熄了灯,站在她身边,瞅着星河蔓延的夜空,和她聊起了星星。 她说天上有个古老的花园,是她家族的人建造的,那片横过夜空的群星,是花园里用来照明的路灯。“可,可是,”我本想纠正道,所有的书上都说,那片璀璨的星群是银河。她没理睬我,眼睛直勾勾望着星空,露出了崇拜的神情。她说星星之间其实很辽阔,并非乌有,那里有美不胜收的很多东西,你们人是看不见的。光是你们人的上帝,没有了光,你们就成了瞎子,但光对我和姐妹们,倒是多余的。 我暗暗吃了一惊。我固然是脑瘫儿,但懂的东西并不比一般人少,我还特别喜欢收集科技新闻剪报。她的话打开了我记忆中的一扇门。我想起了关于“暗物质”的报道,那则新闻是说,除了看得见的星星,宇宙里还有巨量看不见的物质,它们分布于星星之间的辽阔空间…… “天上的大花园,怎么会是你家族的人造的?难道你是从天上来的吗?” 水姑娘可能受不了我质疑的口气,连忙把目光从天上收回来,开诚布公地说,氢原子就是她的祖先,宇宙里所有忙忙碌碌的物质,都是她家族的后代。可是,我明明记得中小学课本上说,水里除了有氢原子还有氧原子。难道氧原子不是她的祖先吗?她笑着回答,这些血亲家谱,你们人是看不出来的,水的家族一直是母系社会,氢原子是水的母亲,喜欢沾花惹草的氧原子,是水的父亲,但家谱从来不会提父亲。她一味谈论母亲的热情,倒无意中帮我缓解了心里的压力。我母亲是个老派人物,一直担心我结不了婚,会断子绝孙。现在,水姑娘的一席话,令我豁然开朗。是啊,真正传种接代的事,也可以看作已由女性完成,我有个身材匀称的妹妹,十年前就已结婚生子,家族其实已无断后之忧。 我顿时变得兴高采烈,忍不住对水姑娘说起了情话。但她脸上的表情异常镇定,说爱上她只会落得个孤单寂寞,千万不要陷进所谓的爱,只有友谊中才有你需要的光亮。话音刚落,我蓦地发现,空地周围的黑暗中真出现了光亮。亮点一对一对地出现,一共出现了四对。那是四只狼的眼睛。我立刻故意提高嗓音,来为自己壮胆,问她看见狼了吗? “哦,是它们。你别动,看我的!” 说罢,她舞得更快了。突然间,瀑布和沿着草地蜿蜒的溪流,变成了一条摇曳的火龙,火龙里的火焰像无数只手臂,竭力在空中抓捞着什么,有十来只还伸向了狼群。那一对对阴森可怖的幽绿光点,一眨眼就不见了,我听见了它们踩着落叶拼命逃窜的脚步声。之后,火龙又变回成了和谐的瀑布和溪流…… “太神奇了!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完全崇拜地看着她。 “这个时候当然就需要父亲来帮忙,因为跳这样的舞需要更多的氧……” 中秋之后,哪怕我在砍伐树木,眼前还是浮动着水姑娘的幻影,亏了她,我才继续撑在那片惨叫的地狱里。随着砍倒的树越来越多,树们的惨叫也越来越高亢、揪心。一旦收工吃完饭,我就赶紧拎着手电,扛着护身的铁锹,去探访水姑娘。水姑娘永远在从容不迫地跳舞,当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会说:“总有一天你要适应没有我的世界,我不会永远在这里跳舞……”我破天荒地没有问她为什么,并非因为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她的舞蹈、风姿,让我看着她的那一刻变得多么开阔啊,让我的心变得多么温暖、安宁啊,我还有必要去纠缠、弄清那未知的未来吗?说来也怪,自从水姑娘用火龙驱走了狼群,我走在漆黑的山路上,内心再也没有了胆怯。我肩上扛着一把铁锹,脑子不再想狼会不会突然跳出来。也许水姑娘就是我的保护神吧,直到伐木工的合同期满,我也没遇到那几条狼。 倒是在一个暮色苍茫的黄昏,看见了伐木工们津津乐道的那一幕:老板和小美人正在瀑布中野合。不知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偷窥的快乐,看见他们肆无忌惮的行为,我本能的反应是愤怒。我拿起一块石头,朝水潭扔去。扑通一声,惊得他俩闪电般分开,各自朝自己的衣服跑去。我扔第三块石头时,老板已经拉着小美人,躲在了一棵大树后面。 “狗日的,是谁在那里扔石头呀?”空气中传来了老板发颤的嗓音。 “狗日的,是我!” 我坦然地走到空地上,眼睛却瞅着瀑布中的水姑娘。她可怜地把自己缩成毛线那么细,完全没有了我崇拜的腰身。是啊,他俩逼人太甚! “是你?你个狗日的没脑子啊,你偷看不说,还坏我的好事!” 我把铁锹往地上一插,摆出示威的架势,说:“瀑布里有我的女友,你们两个敢再欺负她,我就和你们拼了!” 老板慢慢从树后露出了身子,“什么?瀑布里有你的女友?你疯了吧?!”他疑惑地朝瀑布踱过来,然后定定地站在瀑布跟前,左瞅右看。他当然是看不见水姑娘的。 “你看不见的,她是在里面。”说话间,我看见一直躲闪着他俩的水姑娘,慢慢恢复了美丽的原形。我的心又热乎起来。 “噢,太好了,我总算可以透口气了,谢谢你呀!刚才把身子缩那么小,真要憋死我了!” “不用谢!你要是难受我会更难受的。以后我要来这里巡逻,不让别人欺负你!” 我大声对水姑娘说的话,大概吓到了老板,只见他露着不敢相信的神色,来到我跟前,“你到底怎么啦?怎么会对着瀑布说话?这水里啥也没有呀,你是不是……”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但他瞥了一眼我手中的锹,没敢把话说完。 “我女友就在瀑布里,只是你看不见而已,但我能看见。”我说话时的坚定语气,令他的神色更加惊慌。他二话不说,转身一把拉起小美人的手,快步离去,走远了才开始嘟囔道:“他真的疯了,居然跟水说话,居然把水当作他的女友……” 老板辞退我的那天,屋里弥散着一种紧张的气氛。黑而幽深的棚屋里,坐着那几个我早已得罪的伐木工。我看出铁锹就摆在他们脚边不远,而那把我早已用熟的铁锹,不知何时已被人悄悄收走。老板说话十分温和,说生意越来越难做,他不得不减少人手,考虑到是突然通知我,他多发一个月工资作为补偿。我二话不说,噌一声站了起来。老板身边的几个伐木工,立刻紧张地跟着站起来,虎视眈眈地看着我。 我的内心虽然和他们格格不入,但我还是友好地伸出手,想和他们握别。这些平时随随便便、大大咧咧的人,也被这个正式的仪式打动了,他们犹豫片刻,也纷纷伸出手来。他们握手时的力道很大,那种很重的意味,让人感觉就像诀别。轮到老板和我握手时,他软塌塌的手,竟让我突然有点可怜他。那一刻,我强烈地感到,他平时身上散出的匪气,不过是硬撑出来的虚弱。 办完手续,背上行装,我匆匆来到瀑布边,和水姑娘道别。她一边满不在乎地跳着舞,一边脸上挂着泪,却安慰我说,“你不过早走一步,我很快也要走了,就算你不走,我不久也会走的……”我可不喜欢她这么说,我希望她永远这样跳着舞,哪怕只是跳给星星和狼群看。 “别说不吉利的话了,你不会走的,你会永远在这里跳舞!我还会来看你的!”我心里对未来的期待还多着呢。 她笑了起来。她一笑,我们告别的气氛就不那么沉重了。“你就别孩子气了,我真的会走,你也别千里迢迢来看我,到时你也找不到我。”我明白她是怕我太眷念此地,故意说些狠话来缓解我的伤感。后来,我们又聊起了星星,我心里的那份伤楚才有所缓解。是啊,正如她说的,以后只要在家乡看见高高在上的星星,就等于看见了她的家族,看见了她。这么一想,心里似乎就真有了盼头。 临到告别的最后时刻,我从包里掏出廉价的山寨数码手机,满脸通红地问她,能否拍张她的照片留念?她想都没想,就哈哈大笑起来,“谢谢你这么在乎我,可你手上的东西,永远比不上你的记忆,不过你可以试试看!”我不太明白她的话,既然她已同意,我就立刻对着她咔咔咔按下了快门。可接下来出现了十分蹊跷的事,当我打开手机图库查看照片,却只见到漆黑的背景上有成群的星星,完全找不到她身躯的一丝踪迹。我明明对着她拍照,照出的却是群星!我不服气,又试了一次,结果没什么两样。群星绽放出的亮光,成了那些照片的主角。 “还是相信你的记忆吧!”她用手指了指我的脑袋说,“你其实很聪明,以后要多靠它(指脑袋)吃饭,而不是光靠体力。”我觉得她的话像把钻子在钻我的脑壳,一直困顿的心就突然有了通气的感觉,这大概就是书上说的醍醐灌顶吧——她果然不同寻常,超凡入圣…… 我的脑子里还真藏着宝藏呢,我这颗被人称为脑瘫的脑袋,只要盯着一件事总能做到出其不意。返回家乡后,我从不懂电脑到上网开服装网店,只用了区区数月。又过了半年,别人就对我刮目相看了——我看准的衣服式样,总能很快卖出去。忙完年关,望着赚来的花花钞票,心里却有种不相称的感伤。是的,你也许猜到了,我又想起了水姑娘!母亲当然不希望我过年走出家门,但我内心明白,我必须去探访水姑娘,这种事正不断在梦里出现。我说给母亲听的出门理由,颇有说服力——我要去千里之外相亲。母亲原本眼里还噙着泪,一听说我要去相亲,立刻破涕而笑。她转身拉开柜门,用钥匙打开属于她的私人抽屉,摸出一枚色泽暗淡的金戒指,郑重其事地说:“喏,这是你们郭家的传家宝,也是护身符,你这回带上可以保佑你,将来再传给你媳妇……” 我把那枚家族金戒指,藏在衣服靠近心脏的内兜里,迎着喧响的过年爆竹声,出发了。两天之后,我到达了那条瀑布,但我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长发一样飘逸的溪水断流了,瀑布和水姑娘已消失无踪。 我站在干涸的溪流边,一连问了自己二十个为什么?问得自己心急如焚。眼前越是出现水姑娘的幻影,我越是执拗地要找到她。我第一次沿着干涸的溪流往上走,哪怕背着沉重的背包,走得还是飞快。最后,我被沟一样干涸的溪流,引到了山顶,见到了安安静静但残酷的一幕:山泉被粗大的水泥管引向一座工厂,它从工厂出来时已变成血红,被随随便便排向山谷的湖。我站在山顶朝下看,认出湖中漂满水姑娘们的血红内脏,当然,我无法认出哪些内脏属于我心爱的那个水姑娘…… 我心如刀绞。这些漂浮的血红内脏,与周围秀丽的山色多么格格不入啊!我听见自己忍不住在哭,也突然明白了水姑娘说过的那些话。我一直呆到再也看不见那些血红,呆到我和她都熟悉的星星出现在头顶。空气中一直弥散着腥臭,眼前又黑又深的夜色,却向我呈现着迷人的美丽。我迎风站在湖边一块高高的悬崖上,摸出那枚金戒指,铆足了劲,朝湖水扔去。 “它会保佑你!它会保佑你!……” 我知道她暂时听不见,但我会一直喊下去,一直喊到声音能穿过阴阳之间的那堵厚墙…… 黄梵,年生。诗人、小说家。年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飞行力学专业,现为该校文学副教授。 著有《第十一诫》《等待青春消失》《女校先生》《南京哀歌》《浮色》等。 获第二届作家金短篇小说奖等。作品被译成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希腊语、韩语、法语、日语、波斯语等文字。 浮色 中国走族 第十一诫 女校先生 等待青春消失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重磅盘点2016年影响医药行业的十二大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