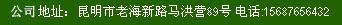|
北京最好的酒渣鼻医院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8598818.html点击
从以上战事来看,左宗棠自从湖南统兵来到赣北后,以少胜多,屡立奇功,深为曾国藩所倚重。曾国藩力挺左宗棠,屡屡向朝廷举荐,使左宗棠得以青云直上,开衙建府,帮助他仅用两、三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别人一辈子也不可能走得完的路程。如果没有左宗棠舍身保祁门,曾国藩则有可能埋忠骨于徽州青山绿水间;如果离开了曾国藩的极力保举,左宗棠极有可能在湘阴柳庄种一辈子地了。可就是这样生死相托、荣辱与共的两位老乡好友,谁能想到,后来却相互交恶,老死不相往来呢?世间事原本就是这样:“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啊!常言道:“文人相轻,自古而已。”曾国藩和左宗棠虽说都是饱读经书之人,甚至是儒理大家,但也摆脱不了士大夫们的这些陋习。左宗棠在营,称呼他人从来都直呼其名,惟对曾国藩客气一点,叫他“涤生”(曾国藩的字)。有一次,两人辩论,互不相让,曾国藩为缓和气氛,便改换话题,说咱们对对子吧,并出了上联:“季子自鸣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意思是说:老左,你别总是牛B哄哄的,非要跟我对着干;联中巧妙地嵌进了“左季高”(左宗棠的字)三个字,算是一半玩笑一半顶真。左宗棠正在气头上,不假思索对了下联:“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他的意思则是,老曾,我看你只不过是口头救国,真论起经世济民之术来,你是屁毛都不懂啊!联中也嵌进了“曾国藩”三个字。曾国藩在联中镶进“左季高”,是只直呼其字,而左宗棠在联中镶进“曾国藩”,却是直呼其名,显得极为无礼。曾国藩本拟借对联化解纷争,孰料引火烧身,反被左宗棠狠狠修理一餐。又有一次,曾国藩去看望左宗棠,见他正给如夫人洗脚,曾国藩便随口说出:“给如夫人洗脚。”左宗棠也立即反唇相讥:“赐同进士出身。”“赐同进士”是曾国藩一生的心病,左宗棠毫不顾忌,直戳他的痛处。 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虽然才华横溢,恃才傲物,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又始终铩羽而还,长期的郁郁不得志和寄人篱下,使他又具有特别敏感的禀性,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他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令人不快。曾国藩曾因此说左宗棠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还有一次,曾国藩出于谦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用了“右仰”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左宗棠的此言传到曾国藩耳里,曾国藩自然心生不快。没想到,文人相轻的酸腐味,在这两个文学泰斗身上更是表露得淋漓尽致。这些只是文人之间的言语之斗,小儿科,无伤大碍。而他俩真正的“死结”,却是来自朝廷上的笔墨官司,至死也未解开,留下了终身遗恨。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就突显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如此同时,左宗棠也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于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朝廷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认为曾国藩奏洪福填积薪自焚茫无实据,而且天京的太平军已被斩杀殆尽的说法也不可靠,清廷让曾国藩从重参办防范不力的湘军将士。 此时,左宗棠唱的这出“对台戏”,无疑是刺向曾国藩的一把利剑。曾国藩平生自诩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这是曾国藩万万不能容忍的。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福填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左宗棠所称天京城破后,洪福填率三千人逃出,不足为据。而且声言,当初左宗棠攻克杭州,有太平军十万之众全数逃出,尚且不被查办,这次逃出几百人也应暂缓参办。言外之意,指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 左宗棠看到此奏后,怎肯善罢甘休?于是又上书数万言为自己辩解,对曾国藩言词激烈,口诛笔伐。至此,曾国藩与左宗棠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虽然左宗棠口口声声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但二人的私交已恩断义绝,从此再无往来,两人十几年的交情因各自之名利而烟消云散了。 名臣毕竟是名臣,他们不会在公务上给对方使绊子,而是秉公说话。左宗棠督陕甘新疆时对友人说:“我和曾国藩不和,如今他总督两江,恐他在饷源上卡我脖子,坏了我的功业。”然而曾国藩却对幕僚说:“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泉恐亦不能为之继。”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不遗余力,并且让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因此,后人评说: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也。左宗棠在西北军营中,一日晚餐后,与幕宾闲谈。左公说:“人们都说曾左,为何不说左曾呢?”众人均无言以对。忽然一少年狂士起身答道:“曾国藩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而左宗棠心目中从来无曾国藩,只此一点,即知天下人何以说曾左而非左曾了!”举座大惊。左宗棠起身拱手谢道:“先生之言是也,曾公生前,我常轻之,曾公死后,我极重之。”确实如此,左宗棠在曾国藩去世时,送给他这样一副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充分表达出自己对曾国藩的由衷敬佩之情和满怀悔恨之意!只可惜,这种“悔恨”实在是来得太晚了点,左宗棠未能当面亲口对曾国藩说,以冰释前嫌,只能闹得一个死不瞑目,另一个含恨九泉,连死了也不得安生,真是“人造孽,不可恕”啊!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的“割袍断义”,从表面来看,是由残留在他们骨子里“文人相轻”的诟病所引发的,“伪幼主案”只是激化矛盾的一个导火索,而实质上,其真实的矛盾冲突还是来自于各自集团的利益所在,正如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左宗棠在给其儿子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曾侯的逝去,我非常之悲痛。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寓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不同的意见,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的。对那些心术不正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左宗棠生性耿直,喜欢有话直说,且又是私底下对其儿子说的,他的这番话应该还是有很高的可信度的。是啊,对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何不一笑置之呢”?还是明代杨慎的词说到我们的心坎上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加入我们 “微祁门”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日本女歌星李香兰ltlt夜来香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