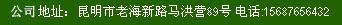|
(-),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年3月20日生于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曾任北京明德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上海法政学院院长,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三届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二任馆长。 (-),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年初前往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年7月离开中央。年11月因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而被开除党籍。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战爆发后,他于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重庆(原四川)江津。年5月逝世。 年10月19日,陈独秀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中统特务联合法租界巡捕房探员逮捕。因陈的身份是平民,又非国民党党员,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批示,由军事法庭初步审问后,转解江苏省高等法院,进行公开审判。江苏省高等法院遂决定以“叛国”罪及“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因陈独秀接受采访时表示无钱请律师,章士钊闻讯后即与陈独秀沟通,义务为其辩护。所谓“顾章与陈之政见,绝不相容,一旦急难,居然援手于不测之渊,斯亦奇矣”,(参见《现代中国名人外史·章士钊》)也正是时人闻此消息后的第一反应。而国民党《中央日报》则在报道中,专门介绍说,章士钊“曾在北京政府时代,历任司法、教育部[总]长职”。(《中央日报》,年11月4日二版) 据《申报》报道,章士钊是在年4月14日开庭前,坐夜车抵达南京。不过,《中央日报》的报道稍有不同。后者说,4月13日章士钊等律师已经去看守所,“交换出庭意见,谈约二小时”。《中央日报》4月15日的报道似乎还有意营造轻松的气氛,说陈独秀等人在江苏地方法院看守所关押的几个月,生活“欢乐”,且引用陈独秀的书信,以资证明。 4月14日上午开庭时,旁听席拥入八、九十人,到4月20日第三次开庭时,更是达二百余人,其中不少是外地专程赶来的旁听者。陈独秀虽请了律师,但仍提供了一份《辩诉状》。因为这份自撰的《辩诉状》与章士钊作为代理律师的辩护词都十分精彩,故一起被沪江大学和东吴大学法学院(均在上海)收入教材之中,供师生研读。 4月20日,也即是在第三次开庭当天下午,先是作为被告的陈独秀进行抗辩。他列举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三大理由,即(1)人民不自由;(2)贪官污吏横行;(3)政府不能彻底抗日。最后指出,法庭的指控根本不能成立。 审理开始,书记官宣布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罪”一案。审判长胡善称命令带陈氏到庭。陈的辩护人章士钊律师入席就座。审判长讯问陈独秀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有无前科后,便请公诉人提出公诉。公诉人朱隽宣读起诉书,认定陈氏犯“危害民国罪”,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提出公诉。 审判长问陈为什么要推翻国民政府。陈朗读他的辩护状回答: 第一,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占东三省,采取不抵抗主义,甚至驯羊般跪倒在日本人之前媚颜投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竟成国民党政府之金科玉律。儿皇帝将重见于今日。”这样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 第二,“国民党吸尽人民脂膏以养兵,挟全国军队以搜括人民,屠杀异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官俱在议亲议贵之列。其对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使之自首告密。此不足消灭真正共产党人,只以破灭廉耻导国人耳。周幽王有监谤之诬,汉武帝有腹诽之罚,彼时固无所谓民主共和也。千年之后之中国,竟重兴此制,不啻证明日本人斥中国非现代国家之非诬。路易十四曾发出狂言‘朕即国家’,而今执此信条者实大有人在。国民党以刺刀削去人民权利,以监狱堵塞人民喉舌。这样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 第三,“连年混战,杀人盈野,饿殍载道,赤地千里。老弱转于沟壑,少壮铤而走险,死于水旱天灾者千万,死于暴政人祸者万千。工农劳苦大众不如牛马,爱国有志之士尽入囹圄。这样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 “国家将亡,民不聊生,予不忍眼见中国人民辗转呼号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 陈氏这番话,博得大众的称赞,觉得他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旁听席上,有的点头,有的微笑,有的对身旁的人小声细语:“对,言之有理。” 接着,审判长又问:“你知不知道,你要推翻国民政府是犯危害民国罪吗?” 陈氏回答:“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此近代国法学者之通论,决非‘共产邪说’也。以言土地,东三省之失于日本,岂独秀之责耶?以言主权,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岂独秀签字者乎?以言人民,予主张建立人民政府,岂残民以逞之徒耶?若谓反对政府即为‘危害民国’,此种逻辑,难免为世人所耻笑。孙中山、黄兴曾反对满靖政府和袁世凯,而后者曾斥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故认为反对政府即为叛国,则孙、黄已两次叛国矣!荒谬绝伦之见也。” 陈氏的话还没有说完,旁听席上已发出了笑声。笑声越来越大,以致审判长胡善称不得不站起来制止。他对陈独秀说:“你只能就你的罪行进行辩护,不得有鼓动的言词。” 陈独秀回答说:“刚才我的话难道不是正对着你们的起诉书所强加给我的罪名进行辩护么?好,你不要我说话,我就不说了。” 胡善称说:“不是不要你说话,只是要你言词检点一点。” 陈氏继续说:“余固无罪,罪在拥护工农大众利益,开罪于国民党而已。予未危害民国,危害民国者,当朝衮衮诸公也。冤狱世代有之,但岂能服天下后世?予身许工农,死不足惜,惟于法理之外,强加予罪,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也。法院欲思对内外保持司法独立之精神,应即宣判予之无罪,并责令政府赔偿予在押期间物质上精神上的损失。” 陈氏说完,章士钊从辩护人席上起立,为陈独秀辩护。他说:“本律师曩在英伦,曾问道于当代法学家戴塞,据谓国家与政府并非一物。国家者,土地、人民、主权之总称也;政府者政党执行政令之组合也。定义既殊,权责有分。是故危害国家土地、主权、人民者叛国罪也;而反对政府者,政见有异也,若视为叛国则大谬矣。今诚执途人而问之,反对政府是否有罪,其人必曰若非疯狂即为白痴,以其违反民主之原则也。英伦为君主立宪之国家,国王尚允许有王之反对党,我国为民主共和国,奈何不能容忍任何政党存在耶?本律师薄识寡闻,实不惑不解也。本法庭总理遗像高悬,国人奉为国父,所著三民主义,党人奉为宝典。总理有云:‘三民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为何总理宣传共产,奉为国父,而独秀宣传共产主义即为危害民国乎?若宣传共产有罪,本律师不得不曰龙头大有人在也。现政府正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予意已成犄角之势,乃欢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乎?今侦骑四出,罗网大张,必欲使有志之士瘐死狱中,何苦来哉?为保存读书种子,予意不惟不应治罪,且宜使深入学术研究,国家民族实利赖焉。总上理由,本律师要求法院宣判独秀无罪。” 据《申报》转发国民党中央社的通稿《陈彭案辩论终结》称,章氏的辩护词持续了五十三分钟。其所讲的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阐述现代国家观和法理,也即讲国家中的公与私的问题,国家与人民、国家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律的适用范围;二是出于直接为陈独秀辩护。这部分更多地是从辩护的策略上考虑。(详见《申报》年4月22日第2张第8版,下同)而也正是后一部分内容引起了陈独秀的不满。 章士钊说,陈独秀反对国民党并没有违背法律,“法律上并无宣传共产党即为犯罪之规定”。他引用孙中山“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好朋友”。同时指出,起诉书中指责陈独秀等人“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贫农”一事不妥,因为孙中山也曾说过,要“分配之社会化,消灭商人的垄断”。他进一步强调说,陈独秀的“托派”主张与国民党在“清共”上正好形成“犄角之势”,意思是有利于国民党“清共”,因而不仅不反国民党,反而应该有功于国民党。 就是这最后一句话,陈独秀当庭否认。他不认为自己是反对共产党的,且以为章的辩词歪曲了自己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主张。所以,在章士钊发言结束后,陈独秀遂声明道:“章律师之辩护,以其个人之观察与批评,贡献法院,全系其个人之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再亦无须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见《陈独秀辩论总结》,《申报》年4月23日第3张第9版) 章士钊的“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下面便是当时登载在《申报》上的章士钊陈案辩护词: 本案当首严言论与行为之别。 言论者何?近世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 而所谓自由,大都指公的方面而言。以云私也,甲之自由。当以不侵乙之自由为限。一涉毁谤,即负罪责。独至于公而不然.一党在朝执政,凡所施设,一任天下之公开评荐。而国会、而新闻纸、而集会、而著书、而私居聚议,无论批评之酷达于何度,只需动因为公,界域得以“政治”二字标之,俱享有充分发表之权。 其在私法,个人所有,几同神圣,一有侵夺,典章随之。以言政权,适反乎是,甲党柄政,不得视所柄为私有,乙党倡言攻之,并有方法,取得国人共同信用,一转移间,政权即为已党所衣。“夺取政权”云云,”夺取”二字、丝毫不含法律意味。设有甲党首领以夺权之罪控乙,于理天下当无此类法院足辩斯狱。 法院之权,尽可推鞠违法之帝王,而独未由扶助怙势不让之政府者,凡政争之通义则然也。往昔囊游英伦,闻教于法家戴塞,彼谓国会改选,两党之多数互易.而在朝党不肯去位,而在野受殊无法律救济之途。诉之法官,法官必无法置对。而英伦自有宪政以来,在朝党从不以不肯去位闻者,全由名誉律为之纲维。故本斯而谈,政权转移之事,移之者绝不以为咎,被移者亦从不以为诟。我往彼来,行乎自然,斯均衡之朋谊,亦作宪之轨。 十八世纪后,欧美国家之逐步繁昌,胥受此义之赐,稍有通识,颇能言之。至若时在二十世纪,号称民国,人民反对政府,初不越言论范围,而法庭遽尔科刑论罪,同类无从援手,正士为之侧目。新国家之气象,黯淡如此,诚非律师之所忍形容。 中国如历代暴主兴文字狱者无论也,欧洲在中古黑暗时期,士或议政,辄遭窜杀;惟英伦自大宪章确立后,“王之反对党”一名词.屹然为政治上之公开用语,人权得所保障,治道于焉大通。各国效法,纷立宪典,遂蔚成今日民权之盛备。倘适伦敦或之纽约,执途人而语之,反对政府应为罪否?将不以为病狂之语,必且谓为侮蔑之词。如本案检察官起诉书:“一面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骂,肆意攻击,综其要旨,则谓国民党政府威信堕地,不能领导群众”云云,曾成为紧急治罪之重要条款。此即仰中外人而互衡之,何度量之相越及公私之不明如是其甚耶!退一步言,如起诉书所称,信得罪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共十一条,究视何条.足资比附耶!讥而言冷,骂而曰热,检察官究以何种标准,定其反对高下之度数耶?要之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即其国应付紧急形势之特点法规,亦未见此项正条。本起诉书之论列,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此首需声明者一。 何谓行为?反对或攻击政府矣,进一步而推翻或颠覆之,斯曰行为。而行为者,有激随法暴之不同,因而法律上之盘意义各别。法者何?如合法之选举是。暴者何?如暴动成革命是。凡所施于政府,效虽如一,而由前曰推翻,由后则曰颠覆。所立之名,于法大不相同.何也?颠覆有罪,推翻势不能有罪。设有罪也,立宪国之政府将永无更迭之日,如之何其能之?查《刑法》第一百零三条内乱罪:“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及政府……”言外之意,凡以合法之方法,更易政府,即无触犯刑章之虞,殊不难因文以见又。 起诉书罪陈独秀有云: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如问此之推翻所取为何道耶?上次庭讯,审判长询及国民会议事,陈独秀答云:“共产/党有权召集,则自行召集之。如由南京国民政府召集,共产/党亦往参加。”由陈独秀之言,绝未自弃其党于普通政党,普通政党以何道取得政权,共产/党亦遵行之。此观各国议会,无不有共产/党之席次,共产/党之下,选区争选票,一是与他党同。可见共产/党所取政权之第一大道,仍不外法定之选民投票,即陈独秀之意亦然。 国民党政府虽以训政相标榜,而训政有期,与美国总统之任期相若。孙中山先生恒言,天下为公,唯德与能。无论党中何人,俱无国民党永久执拿政权之表示。公文书中,亦无此类规定。最近开放政权之声,尤县嚣尘上,训政之期,无形缩短;每年一开之本党代表大会,今为还政于民之故,亦正议提前。在若此情形之下,有人谋代国民党而起,易用他种政体以行使准备交迁之政权,何得为罪? 审判长郑重问陈独秀云:“共产/党最终之目的是推翻国民党建设苏维埃否?”答云:“当然,惟非最终目的耳。”夫“推翻”二字,虽于耳未顺,然若英伦法官问保守党员云:“保守党之目的,是椎翻自由党建设巴尔温内阁否?”此除“当然”以外,当无异答。遽科为罪,宁非滑稽之尤? 或曰不然,陈独秀所云,乃暴动斗。比在供词中,侃侃言之,何止一次?故起诉书曾切曰:“应由其领导农工及无产阶级等,以武装暴动,组织农工军,设立苏维埃政权。”争选无罪,暴动岂得无罪乎?曰:是立分别言之,陈独秀之暴动,谓与国民党打倒北洋军阀时所用之策略正同,核之恒人心理中之杀人放火,相去绝远。且亦只谓“应”如何而已,谓之曰应,是理想,不是事实。又属应为,其在将来.而不在今日甚明。《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以“左列行为”为必要条件。左列行为者,指现在之事实。反之,同为暴动,而不过未来之理想者,其将不在本条论域之内、初不得课识之士而知之。独秀虽不否认暴动,而当度一再供称力量不足,并无何项暴动,江西一地之共党,与彼等意见不一致,绝未参加.亦从未派人前往视察,至于正式红军,须在取得政权后,始行组织,此时尚谈不到。党中组织,完全独立,经费由党员节衣缩食充之,不受第三国际之一毫接济等情。是“暴动”云云,亦揣想将来必经之阶段而已,与目前之治安,了无连谊。所谓扰乱(《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一条)国宪如何,毫不生影响。所谓紊乱《刑法》第一百〇三条内乱罪)如何牵连误会,始得羼入紧急内乱之范围。律师不教,窃所未渝。 大法律之事,课现在不深将来。春秋诛心,有君亲无将之义,黍立暴虐,方腹诽必禁之余。此一为相祈经说,一为专制淫威,律以近世发现其实之《刑法》要旨,相去何万世。本庭遗像昭垂之孙中山先生.即倡言共产主义者也。特叮咛以示于众曰:“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以故先生所持共产理论最近底而流弊毫无。如谓将来之举动,当受刑事制裁,则以共产嫌疑先陈独秀而应被处分之人,恐非法庭之力所能追溯。若州言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绳之法律平等之谊,又焉可通? 综上所言,陈独秀之主暴动,即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之“行为”两宁、合义迥不相眸。是以行为论,独秀亦断无科罪理。此应声明者二。 及次,起诉书所引罪名,一则曰叛国,再则曰危害民国。窃思国家作何解释,应为法院之所熟知。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夫国者,民国也,主权在民,时曰国体,必也于民本大有抵触,如运动复辟之类,始子为叛.始得溢为危害。自若以下,不问对于政府及政府个何人何党,有何抨击,举为政治经社中必出之途。临之以刑,惟内崇阴谋,外肆虐政,一大半开化之国为然,以云法制,断无此象。从独秀之所以开罪于政府者,非以其鼓吹共产主义乎?若而主义,由司立之眼光视之,非以其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乎?(检察官以《紧急治罪法》第六条起诉)如实论之,尤谬不然。孙先生之讲民生主义也,升京明义之言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第一讲首段)其解释同党之误会云:“许多同志,因为反对共产/党,便居然说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同。“(第二讲)下又云:“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杜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又云:“国民党既是赞成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之目的,就是会众人能够共产。”(同上) 综合前后所论、其说明民生过程共产相同及相质相别之处,何等明切。今孙先生之讲义,全国弦诵,奉为宝典,而陈独秀之杂志,此物此志,乃竟大干刑辟,身幽囹圄。天下不平之事。孰过于斯? 又起诉书指独秀“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贫农,其言词背谬,显欲破坏中国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此即《中山丛书》求之,复如桴鼓之应,不差累黍。民生主义第一讲云:“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总是相冲突,不能调合,所以便起战争。最好是分配之社会化,消灭商人的垄断。’斯与起诉书中上述各语,论质论量,俱不知有何分殊。尤为彰明较著者,同盟会之四大政纲,第四即日平均地权,既曰平均,当日分配,后有分配,其先必有没收。没收者何?取之地主之谓。分配者何?给与贫农之谓。商人的垄断于焉消灭,劳工之冲突,于焉化除。中国传统至今之经济政治两种组织,如之何其不破坏乎?援陈证孙,本如一鼻孔出气,谓是言词背谬。龙头大有其人。 尤有足资记注者,孙先生平均地权之策,至今迄未实行,其所以然,则曩述“共将来不共现在”一语,足为铁板注脚。惟其如是,故孙先生时时以“革命尚未成功”一语强聒于众。盖平均地权之业,须以革命之力成之,理势则然也。夫孙先生之革命,与陈独秀之暴动,一贯之论尔。孙先生之书,既为国人所诵习,既其革命方略,亦谆嘱同志努力为之。独陈独秀以含义悉同之“暴动”字样,求民生主义内之同一中坚政策实现。乍一启口.陷阱生焉,凡服膺中山主义之忠实信徒,其谓之何?且也,就陈独秀、彭述之连日口供观之,此二人者,并不得视为表里如一,首尾一贯之共产/党,何以明其然也? 独秀不认危害民国,而认反对国民党政府。综其理由,约分三事: 一、刺刀政治。政府以强暴之力强抑天下人之口,使不得有所论列。微论非党人之无言论自由权也,即高级国民党员之无枪杆者,亦禁阻使不得声。 二、搜括手段。凡国民党之政策,悉以构成,苛捐杂税,横征无已,聚敛所得,悉数寄存外国银行,以便帝国主义者之操纵把持,侵压本邦,反之,商市萧条,农村破产,国民经济之如何衰败,举不值国民党政府之一顾。 三、抗日无诚意。当人民一致抗声浪最高之顷,政府竟听孤军转战,不予接济,民既剥夺殆尽,民族主义且无以自恃;甚至民间宣言攘外,驳骚有得罪政府之势。彭述之所供略同。此之论调,盖已离却共产/党本位,与一般讥切时政之声口,仿佛一气。如西南五省,如冯玉祥先生,与共产/党风牛马不相及者,近时箴规政府之文电,遍载于南北新闻纸类,亦殊去上陈三事不远。 假令吾国国体未改,帝制依然,以此置于汉人论时事疏,或宋人上皇帝书中,匪惟责罚无闻,抑且优旨嘉奖,事例颇多,无可抵谰。至各国国会,即前席陈词;所为推排当局,惟一时舌锋是视者,其类此之论,尤难枚举。 独是中华,忝为民国,陈、彭言虽稍激,议实从同。以此列为罪状,写入爰书,其以示天下后世?明代于谦之狱,熊廷弼之狱,当时推问,并不限于中涓,狱成之日,何尝不以为罪人斯得,然朝局一变,是非大白,至今公论如何,宁待考知。以今例昔,事同一例。何况陈独秀之于国民党也,今虽仳离,始则合作。 审判长屡讯陈独秀曾否在国民党担任职务?独秀坚称无有。如实论之,却不尽然。所供民国十年在广东任教育厅长,是为孙大元帅在粤确定政权之始,且不具论。而十一年之赴莫斯科,为国民党容共政策所由发韧,同行者且为今日全国之最高军事长官,谈士类能言之。尤要者,十六年四月五日,独秀与今行政院长汪精卫先生发布《国共两党领袖宣言》,首称:“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并云:“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主张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由是推测,可见共产/党中眼光错误,主张打倒国民党者,大有人在,而独秀苦口劝之,情见乎词,至哀告同志,使勿“为亲者所怨,仇者所快。”即此一点,殊足酿成共产党分裂之势而有余。 审判长又问独秀:“究以何故成为苏俄干部派(即斯丹林派)之反对派?”独秀答云:“以意见不同耳。”再问是何意见?即惨然不答,并求审判长勿复进叩党事,致陷彼于自作侦探之嫌。此其哀情苦志,实已洋溢言表。而独秀党籍之被开除,与联合汪精卫发表宣言一事之不见悦于莫斯科干部派人物,不无草蛇灰线,因果相寻之迹,明眼者不难一目得之。己虽不言,而要不失为法院应采之证。当是时也,容共为国民党公开政策,凡共产/党同时为国民党,反之,凡国民党亦多同时为共产/党。陈独秀适为大团结中之一人,其地位与当今国民党诸要人,雅无二致。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已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集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即此以论功罪,其谓托洛斯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此义独秀必不自承,而法院裁决是案,倘不注意及此,证据、方法既有所未备,裁判意旨复不得谓之公平。 要而言之,陈独秀之不能与国民党取同一之态度,势为之也;其忠于主义,仍继续研究共产学说者,理为之也。彼将实行计划,付之后来,与江西红军无关,与第三国际复无关,以托洛斯基自号厥派,实与生物学家之奉达尔文,心理学家之奉佛洛伊德无异,而亦中山之遗教如是。国民党人且当奉行唯谨,矧在他人,至其见到国民党之失政,引绳批杷,有所抨击,此国民之义务如是,即不为共产党,亦得激于忠义而为之。 政府现时约束舆论,刻意从严,如陈独秀所陈三事,未便公开如量发布,则有政府所颁之《出版法》,当然与其他新闻杂志等一律取缔。必欲侦骑四出,如临大敌,一有索引,辄论大刑,国家立法之本旨,岂其如是? 基上论述,本案陈独秀、彭述之部分,检察官征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及第六条,所谓叛国、危害民国及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同之主义,湛然无据,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恬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实为公德两便,谨状。 这篇章士钊为陈独秀的辩护词,虽然写在八十多年前,但颇具时代意义。其中的很多观点振聋发聩,今天依然震动人心。 章士钊在这篇辩词中说的两个问题:(一)对公言论不可入罪;(二)政府不是国家。 这篇辩词理论功底扎实、文采斐然,轰动一时。中外报纸竞相登载。 章士钊在辩词中说“言论者何?近世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 而所谓自由,大都指公的方面而言。以云私也,甲之自由。当以不侵乙之自由为限。一涉毁谤,即负罪责。独至于公而不然.一党在朝执政,凡所施设,一任天下之公开评荐。而国会、而新闻纸、而集会、而著书、而私居聚议,无论批评之酷达于何度,只需动因为公,界域得以“政治”二字标之,俱享有充分发表之权。 其在私法,个人所有,几同神圣,一有侵夺,典章随之。以言政权,适反乎是,甲党柄政,不得视所柄为私有,乙党倡言攻之,并有方法,取得国人共同信用,一转移间,政权即为已党所衣。“夺取政权”云云,”夺取”二字、丝毫不含法律意味。设有甲党首领以夺权之罪控乙,于理天下当无此类法院足辩斯狱。” 他将言论分成公、私两个领域。私人言论领域,以不侵别人的自由为限。一旦构成诽谤,即应当负法律责任。但在公共领域不同,一个政党当朝执政,所有行为都要任人评说,无论批评达到多么严酷的地步,也都应当享有充分的自由。想起今天有些官员,动辄以自己的名誉权、隐私权受到侵犯为由拒绝监督和披露,章士钊的辩词多么有针对性呀!进入到公共的政治生活领域,个人的权利就要被削减,否则不要来当官。这种批评、指责、谩骂、质疑、造谣,不仅不能够禁止,而且要用新闻、出版等法律加以保护。因为这是公共的言论领域,与对私人的领域不同。 章士钊的另一个观点,今天也大有意义:政府不是国家。“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反对政府不是反对国家。政府可以变来变去,国家还是一个。所以他认为陈独秀无罪。陈反对的是国民党政府,又不是中华民国。他在辩词里说:你到伦敦或者纽约的街头,随便拉住一个人问他,如果你说反对政府就是反对国家,他一定会认为你是疯子。 陈独秀被控违反的是国民政府年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第二条和第六条。 第二条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一)煽惑他人扰乱治安,或与叛徒勾结者。(二)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 第六条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章士钊主张对公言论不能入罪,但第二条明确规定“宣传”是可以定罪的。辩词所说的是法理,抨击的是立法。国民党的议会为什么会颁布这样的法律?应当谴责。但这不是司法的事情。 陈案一审判决后,国民党《中央日报》接连发表社评,抨击章士钊有答辩词中的“国家与政府”论,章不服,在5月4日的《中央日报》上引用《中华民国约法》,重申有关法理依据,并指责该报评论员在案件上诉阶段干预法律。 当然,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所有的司法辩护都无济于事。年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仍以“叛国”罪及“危害民国”罪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十三年。随后陈独秀上诉,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迫于各方的压力,改判为有期徒刑八年。直到年“七七”事变爆发,陈独秀才被保释出狱。 [1]第五次被捕经过参见胡明:《陈独秀20世纪30年代的被捕与法庭上的斗争》载于《殷都学刊》年04期第53-58页。[2]年10月24日《申报》。[3]傅斯年原话见于《独立评论》第24号年第10期第2-7页。[4]胡适关于陈独秀的评论参见陈东晓:《民国丛书第一编:第87号·陈独秀评论》上海书店第51-57页。[5]陈东晓:《民国丛书第一编:第87号·陈独秀评论》上海书店第-页。[6]卢天然:《试探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认同——以“陈彭案”为中心》载于《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年02期第-页。[7]祝彦:《年陈独秀在国民党法庭上》载于《报刊荟萃》年04期。[8]汪金山:《国民党未杀害陈独秀之因》载于《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04期第49-50页。 臧启玉讲法律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anhuishengzx.com/ahsh/11068.html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新闻是时候给这些港独分子一次彻底的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