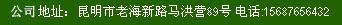|
(本文原载于上观新闻) 摘要她是《乡村爱情》里的“王小蒙”,是《推拿》里的“金嫣”,更是舞剧《青衣》里的“筱燕秋”。 每次演出时,“王亚彬都不再是现实中的王亚彬”,角色的命运浮沉、她对角色的理解、创作时的孤独感受交织在一起,舞者用叠加的肢体语言讲述了自己的生命寄托。她是舞剧《青衣》里的“筱燕秋”,是《乡村爱情》里的“王小蒙”,也是《推拿》里的“金嫣”。舞者、演员、编舞、书的作者……习舞26年的王亚彬有很多身份。 24日下午,喜爱分享与表达的王亚彬作客思南读书会,带着10月出版的新书《生命该如何寄托》,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聊聊“舞蹈”之于她的意义。对谈现场座无虚席,来得早的听众占满了离舞蹈家最近的前排位置;来得晚的,不少人就在门边站着听完了全场。 王亚彬在思南读书会 疼痛是舞者身体的包浆 疼痛,是舞蹈渗透身体的开始。 23年前,9岁的王亚彬考进北京舞蹈学院,身高只有1米36的她是班级里年龄最小的一个。“舞者的第一个工作是解放身体,使身体达到自由的状态。”现在的王亚彬已经可以轻描淡写地说起练舞过程中的艰辛,低年级时,一切动作基础要从地面练起,她们每天要光着腿,只穿一双小袜和地板亲密接触,进行勾绷脚、横竖叉、地面环动、下腰等舞蹈基础训练。 《生命该如何寄托》一书是王亚彬作为一名舞者的思想手记,她用“隐忍的生命之痛”作为书的第一部分内容,因为“疼痛”是舞者实实在在的真切感受。在书里,她还原记忆:练舞时身体与地面的摩擦会刮起木地板上的刺,紧接着刺就无声地落进皮肉里,所以低班学生的课后娱乐就是凑在一起,相互合作用针挑出刺,然后皮肤上就留下红肿的一片。“尽管学校的艺术氛围和环境很好,但在钢琴伴奏老师的音乐声里,总能听到隔壁小孩子压腿时的哭喊声。” 等到慢慢长大了,在舞蹈创作方面,如何挑选合适的肢体语言表现人物,王亚彬有时候也“难免走入死胡同”,“这时候的疼痛是心理上的。” “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一直有种很纠结的疼痛。”仔细读完王亚彬的书,毛时安被“疼痛”二字深深打动,“我拍过一张舞蹈演员休息时的照片,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双脚都有伤痕,每一双脚都缠着膏药,每一双脚都有多多少少的变形。”但舞台上,舞者却永远只把最美的肢体语言献给观众。“舞蹈,是舞者用生命熬出来的美丽鲜花。”毛时安说。 在残酷的淘汰制中,王亚彬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起码没有因为伤痛而离开舞蹈。”历尽艰辛过后,茧子、淤青、色斑成为了舞者身体的包浆,只有舞者知道身体包浆的味道是疼痛的、辛辣的、折磨的。“但不去浸透这样的包浆,却永远无法重生。” 我选择了舞蹈,舞蹈也选择了我 19岁,王亚彬本科毕业,她觉得舞蹈好像与自己走得更近了,自己对舞蹈的了解和感情也更深了。“我不愿意在家里等着编舞来找我,我希望有能力去创造和选择自己想做的东西,通过作品去回答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跳舞?” 年,王亚彬取得北京电影学院硕士学位,并创建了亚彬舞影工作室——“亚彬和她的朋友们”艺术品牌系列演出平台。第一季舞作《与你·共舞》同年在朝阳9剧场演出,现场座无虚席,王亚彬让小提琴、古筝、马头琴成为现场舞蹈表演元素的一部分,将演奏家的行为与舞蹈编织在一起创意了“控制”、“相生”等作品。 “亚彬和她的朋友们”诞生之时,中国现代舞的环境尚未成熟,演出经费成为最大的困难。王亚彬用“到处化缘”形容当时的情景:一部分经费来自舞者自己的投入,一部分来自品牌的赞助,剩下的则来自有艺术情怀的朋友们。但观众的认可是最好的鼓励。王亚彬回忆起有次演出结束时,一对外国夫妇特意在楼道里等演员们出来,并告诉她们:在北京很多年了,都没有看到这么好的演出。“肢体语言或许是最国际化的交流方式。”王亚彬说。 从《与你·共舞》到第二季《寻》、第三季《守望》,再到今年的第八季《M—道》,“亚彬和她的朋友们”走过了八年的时间,经受住了岁月的洗礼。“舞蹈、编舞其实是追求真理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创造历史,而不是重复历史。跳舞成为我们了解未知世界的钥匙,如此,我们了解舞蹈的过去、欣赏现在,同时对于探求未来充满了想象。”王亚彬说。 “我有许多可以选择的方向,可以进行不同的发展。为什么还是选择舞蹈这条最艰难的艺术之路?归根结底是因为热爱。”从舞者到影视演员,再回归舞者,既可以说是王亚彬选择了舞蹈,也可以说舞蹈选择了王亚彬。 生命以舞蹈寄托 “对舞蹈创作者和表演者而言,呈现‘美’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我更希望通过作品传递思想层面的思考。”年10月4日,王亚彬编舞、导演的舞剧《青衣》在国家大剧院正式公演,10位舞者通过戏中戏、日常生活、潜意识和超现实三条线索的有效编织来完成故事的讲述。这部由根据作家毕飞宇小说《青衣》改编的舞剧,呈现的正是舞者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思考。 王亚彬说,自己与《青衣》结缘是在年的南京,当时她受导演康洪雷之邀,加入作家毕飞宇小说《推拿》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剧组,出演盲人按摩师“金嫣”一角。拍摄期间,除了阅读《推拿》的原著外,也读了作家的其他作品,其中就有中篇小说《青衣》。 小说读到一半,在南京梧桐树的摇曳下,文字幻化成了舞台场景的想象,“小说的文字非常有温度,对女性人物的内心描写很极致、细腻,特别适合舞剧表达的特性。”王亚彬看到了青衣“筱燕秋”所探寻的正是“生命该如何寄托”这一主题,这一刻,舞者与书中青衣形成了共鸣。“筱燕秋对艺术很痴迷,这一点,我们很像。不同的是在探讨如何寄托生命的时刻,她选择了身体的声音,而我选择了身体的姿态。” 舞台上,大雪纷飞的冬日,“筱燕秋”拖着长长的水袖,像一张纸艰难地飘出剧场,为了上戏,她减肥、堕胎,忍受了作为人可以忍受的一切疼痛,但命运始终没有眷顾这位悲剧的女性。“每次跳到结尾的时候,我都会潸然泪下。我好像顺着故事的发展脉络,逐渐进入这个人的年轻时代、中年时代以及心态上的老年时代。”王亚彬感慨,演出时的自己不是现实中的自己了。“我穿上水袖,觉得自己变得那么长,可以触碰皎洁的月容,可以深探落寞的湖底,可以依偎壮硕的山峦……” 舞剧《青衣》是王亚彬的首部导演作品。在舞台视觉上,《青衣》以极简主义风格表达人物世界,镜面成为舞台置景、道具运用的最重要元素。在书里,王亚彬写道,“小说《青衣》是中国的故事,但不仅仅是民族的,也不单就是女性的,而是关于一个人的困境,是描述人性的。”人性是共通的,于是,在面对作品时,王亚彬邀请国际化的设计团队,以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希望这样的组合能把舞剧《青衣》带到更广阔的天地。 作为舞者,王亚彬认为现场舞蹈表演的魅力无法取代:“舞蹈的意象是通过肢体语言的叠加,通过个体观看者的思维而产生了不同的意义。舞蹈现场表演的每一场都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又是稍纵即逝的,现场的表演艺术是不可复制和模仿的,这让舞蹈本身表达既定编舞内容时充满新鲜感、神秘感和唯一性。” 三十而立,这个年纪对一个舞者来讲不算年轻了。王亚彬笑言,自己常被同事开玩笑,形容为“一个老的年轻演员”,但她在经过这些年的创作之后,反而不觉得很着急了。生命该如何寄托?现在先提一个问句,“可能再过十年、十五年,我可以再写一本书来作答——生命以舞蹈寄托。” (文:张熠) 在思南阅读世界感谢北京去哪里医院治疗白癜风小儿白癜风如何治疗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1小时温州到杭州的梦想又近了
- 下一篇文章: 朱胜萱造个贴近自然的乐园,再把它送给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