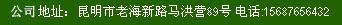|
点击
曾因事出室,湘绮起视所写为何,则满案皆“谬”字。曾复入,湘绮论事如故,然已知曾不能用,无复入世心矣。 二十多岁的王闿运肆口高谈阔论,四十多岁的曾国藩洗耳恭听,且边听边记——这一道特殊的风景,表明王闿运极为自负,颇有效法东晋王猛扪虱而谈的策士风采,但殊不知在饱经忧患、锋芒内敛、已近“知天命”之年的曾国藩总督面前,作“扪虱而谈”之状,岂不是在孔明面前扮演诸葛亮乎?这就不免近似于盲人摸象腿了。 曾国藩不露声色、洗耳恭听的神态,与直截了当在案上所批写的“谬”字断语之间的反差,乃是一种火烧冰淇淋似的强烈反差,令人深可赏玩之余,不禁感叹:即便是绑来黑旋风李逵与白雪公主配戏所凸现出来的反差效果亦望尘莫及。不难想象,当年王闿运在曾国藩暂时告退时,喜滋滋起身探头一望,原以为曾氏执笔恭录的会是一篇王氏“隆中对”,未料竟是满案的“谬”字,这种心理期望值上的突然塌方亦不亚于五雷轰顶,王闿运竟然没有一惊蹶倒而气得脑中风。王闿运的临危不动,神色如常,实在是让人不胜佩服这位湖南佬神经之顽强与坚韧。 咸丰八年秋季,曾国藩驻军江西建昌,不久,湘军在三河镇大败。十二月,王闿运赶至建昌,停留五日,与曾国藩“谈至三更”。当时“曾率羸军饥卒居城旁,寒日漠漠如塞外沙霜。”光景异常惨淡,王曾两人亦可说是患难之交。 咸丰十年四月,战场形势发生微妙变化,曾国藩“奉旨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王闿运见湘军实力渐强,曾国藩又大权在握,于是想投奔曾国藩出谋划策,作为晋身之阶。据《曾国藩日记》所载,王闿运于此年六月初八日开始,在祁门大营勾留达两个多月之久,与曾国藩促膝深谈达数十次之多,几近通宵达旦。他俩大谈、畅谈什么呢?日记中只字未提,一点也不合乎曾国藩记日记的习惯,非比寻常,绝对是不可示人的天大秘密,也绝不可留把柄于他人的灾祸之据,那应是王闿运苦口婆心地劝说曾国藩举兵起事,坐拥东南半壁江山。 湘军攻下南京,王闿运找到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又旧事重提,鼓动他乘机推翻清廷。湘军很多将领都赞同王闿运的主张,可是谁也不敢去说服曾国藩,于是王闿运再次登门劝说曾国藩。这一次曾国藩仍不做声,只是用手指蘸茶汁在桌上大书特书一“妄”字,王闿运见状,愤然离去,后来在对学生讲学时说:“曾大(指曾国藩)不识抬举!”当时敢以如此口气轻蔑曾国藩的人,恐怕天下屈指可数了。 王闿运认为:太平军攻打清王朝,与你何干?谁要你曾国藩半路杀出,来挽救将倾之大厦?因而曾国藩在江西时军事迭遭挫败,内心悲苦凄凉,皆是自讨苦吃,对于汉民族的发展并无一点帮助。此即所谓“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补”之深意。曾国藩助桀为虐之举,不仅于汉民族无益,而且就是对汉人曾国藩本身亦没有益处,反而有许多损害,那便是曾国藩在击败太平天国过程中,清王朝对其重重猜忌、掣肘及防范,以致他常常有岌岌自危之感。同治二年正月七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悲叹道:“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收场耳。” 而王闿运所言曾国藩“与渠亦无济,反有损”之语,确是一针见血,可谓对曾国藩极尽针贬揶揄之能事。于是,王闿运据此给曾国藩盖棺论定:曾涤生一生事业被其谨小慎微的作风所耽误,所以拥有重兵却不敢作天下第一人想,只得俯首替满清王朝卖命,下死力与太平军作战,搞得海内横尸遍野,万民涂炭,还欣欣然自以为对国家民族有功,问心无愧,这岂不就是“儒者”的罪过吗? 同治十一年(年)三月,多年积劳成疾的曾国藩逝世,王闿运亦应景送了幅挽联:“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经术在纪河间、阮仪徵而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限礼堂书。”上联是说曾国藩,虽想学汉朝的霍光,明朝的张居正,可惜时世不同,际遇各异,只能做到底定东南,勋绩不过方面一隅,以宰相的职位,没有机会能象霍光、张居正那样,有继往开来,笼罩全局的相业。下联用的是郑康成的典故,说曾国藩在经学方面的造诣,超过乾隆年间的纪昀和嘉庆年间的阮元,可惜象郑康成那样,因为“岁至龙蛇贤人嗟”,合当命终,来不及把他置在习礼堂上,残缺不全的书籍,重新整理,嘉惠后学。换句话说,曾国藩倘能晚死几年,必有一些经学方面的著作传留下来。此联写得意味深长,表面上抬出一连串历史名人与曾国藩相提并论,但究其实,笔法却寓贬于褒:“上联讥其无相业,下联讥其无著述。”曾纪泽看到此联后,则大怒,骂王闿运“诚妄人而已矣”,当场就把此联撕毁了。据说,王闿运的这幅挽联可把曾大人害惨了:相传到了光绪年间,有人向清廷建议,应该批准将曾国藩放入文庙,一起祭祀。清廷回话说,那就由礼部议一议,先拿出个初步意见,供朝廷参考吧。礼部讨论时就有人说:国藩既无著述问世,于经学方面又无发明,并举王闿运的这幅挽词为证,言之凿凿,此事也就因之而作罢了,害得曾文正公吃不到文庙里那些冷猪头肉等祭品。 光绪三年(年),曾纪泽为了表彰曾家平定太平天国的功劳,以六千银元的代价请王闿运编撰《湘军志》。那知王闿运在写《湘军志》时,来个秉笔直书,有时还借用一下“春秋笔法”,寓褒贬于文字之间。王闿运首先对湘军在攻破天京之后,大肆烧杀抢掠予以揭露,认为江南的财富被湘军劫掠殆尽。又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很多不是。李秀成被其俘获后,本来要押送北京,当曾国荃看到许多投降的太平军将士一见李秀成便跪拜时,便心存忌恨,擅自将李秀成杀害了。当时名将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霖、鲍超等人都不满曾家兄弟的做法,欲离营而去。王闿运在《湘军志·筹饷篇》中又说,曾国荃家中有良田百余顷,于法应当上田赋册,但当地官吏畏惧他的权势,不敢过问,更不敢上门征税。曾国荃等人审阅后,恼羞成怒,并斥责王闿运“虚诬”,说《湘军志》是一部“谤书”。此事引起原湘军头面人物极大不满,纷纷指责王闿运,其中尤以曾国藩亲家郭嵩焘为甚,说:“壬秋文笔高朗,而专喜讥贬。……张笠臣指为诬善之书。”不久,郭嵩焘将刻版烧毁。 由于王闿运在《湘军志》以及其他不同场合中贬低讥刺曾氏兄弟,引起湘中士林的不满乃至驳斥。在追怀前尘之时,湘中人士越发佩服曾国藩当年弃用王闿运的知人之明,如曾参与纂修《江南通志》的安徽巡抚冯煦就说:“文正当日,凡湘中才俊,无不延揽。而对于此老,则淡泊遇之如此。益服文正之知人。” 王闿运汲汲要充当曾国藩的诸葛亮,献奇计,建异策,撺掇他造反自开新局面,然而这位纶巾羽扇之客是否替他的曾姓东翁切过脉搏,仔仔细细地了解过曾国藩的肝胆心肺、血脉脑髓呢?看来没有。曾国藩是“诸葛一生唯谨慎”,为人处世崇尚“扎硬寨,打死仗”,力求步步为营,不喜冒险;在官场宦海之中又深得老聃守雌谦退之道。况且,他经过多年浴血奋战,好不容易在祁门大营中刚刚得了个两江总督的显耀官职,印柄子还没握热,总督的宝座还没坐滚,岂能轻易听从你王闿运舌底翻澜、怂恿造反?轻冒株连九族之险,去进行一场毫无把握的政治豪赌? 总之,王闿运对于曾国藩的认识是相当肤浅的。但是,曾国藩对于这位王姓湖南同乡的肺腑禀性却有入木三分的认识。这里插个小故事,可窥一斑以见全豹,此事见于汪辟疆的《光宣以来诗坛旁记》: 徽府失守,祁门战事吃紧。大战前夕,王湘绮适客军中。曾国藩知道恶战在即,就借各种差事名义遣散幕府文士,不想让这些人毁于战火。李鸿裔知道曾国藩的心思,可又没见他打发王湘绮离开,就提醒曾国藩说:“王壬秋也在这里,你为什么不让他走呢?”曾国藩说:“我幕中的文士,打发他们离开的时候,都是以办事的名义,没有露出有意安排他们离开的痕迹,因而没有引起军心的动摇。壬秋是以作客的身份到我这里来的,突然送他离开,我担心引起连锁反应。不过壬秋一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你试着去看一看他那里的情况,回来后告诉我。”李鸿裔在王湘绮那里看到他正在聚精会神地读《汉书》的情景,回来后就把自己的所见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笑着说:“王壬秋就要走了。”过了一阵子,曾国藩得到报告,说是王湘绮已离开祁门到别处去了。李鸿裔很是不解,就问曾国藩:“你是怎么知道王湘绮要离开的?”曾国藩回答说:“王壬秋是饱学之士啊,他又不是没见过《汉书》,为什么那么专注呢?他是在借看书做掩护,作自己如何摆脱困境的打算啊。”真可谓“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呵! 曾国藩察人如此细微,料人如此神奇,大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料定曹阿瞒在兵败赤壁之后,必走华容道之风采呵! 早年王闿运饱读经史而惊才艳艳,时人赞誉他:“湖岳英灵郁久必发,其在子乎!”然而这位由三湘之地灵气所钟的王姓大才子内心世界的云山雾嶂、通幽曲径,竟被曾国藩在谈笑之中一眼看穿,一语道破。夫复何言?不禁使人肃然起敬:此公阅尽古今荣枯、盈亏、雌雄、黑白等权变机诈之道,饱知世间人情诚伪、巧拙之态,识人之深,驭人之巧,老辣如此,狡黠如此,岂是高卧隆中的羽扇纶巾之士所能限量?确如民间传言,乃是洞庭湖中载沉载浮、潜修八百年的蟒蛇精怪投胎转世也。 加入我们 “微祁门”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岁末年初,环保厅长的那些变数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